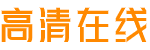座談會現場
7月13日,“大慶故事:中國式現代化的國家與個人”座談會,在北京三聯韜奮書店美術館店舉行。哈佛大學設計研究生院講師侯麗、中國城市規劃設計院院長王凱、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嚴鵬,以大慶這座獨特的工業城市為切入點,通過多維度的探討和分享,為公眾提供一個深入了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機會,為思考未來發展道路提供有益啟示。座談會由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王洪喆主持。
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王洪喆
今年6月,以大慶油田為背景,深入探討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的史詩性著作《大慶:為了石油的建設》,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發行。該書作者侯麗,現執教于哈佛大學設計研究生院,研究興趣主要在城鄉規劃歷史與理論、共和國城鎮化與工業化歷史、城市政治等。
《大慶:為了石油的建設》 侯麗 著 張歡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4-6
作為一本城市史研究的別致之作,《大慶:為了石油的建設》講述了關于大慶油田這座模范“城市”如何成為時代工業地標的故事。有評論指出,國外關于城市的書籍非常多,但中國學者寫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而且和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如此密切的著作卻不多見。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書中采用雙線敘事,一方面透過大慶城市的設計與建設,折射出新中國前三十年歷史環境變化及政治路線選擇;另一方面通過女規劃師曉華的個人經歷,講述她在大慶的工作、生活與大歷史中的個體抉擇。如此雙線交織、互為補充,為過往早已被宏大敘事塑形的歷史,注入了其間個體參與者的情感與溫度。
“個人的角度是這本書重要的切入點和貢獻”
座談會上,侯麗首先發言。她表示自己寫作該書的初衷,“就是希望展現大慶除了戰天斗地之外更加多面性的故事,從多個角度講大慶的故事。說起來,我這個70后也是石油子弟,從小在勝利油田長大。我也常會去思考現代化進程中國家敘事和個人命運如何交織在一起,因而這本書一個重要的切入點或者說它的一個貢獻,也是個人的角度。”
哈佛大學設計研究生院講師侯麗
“過往我接受的學術訓練是作為規劃師,探討的多是國家的使命、國家的敘事、空間秩序的塑造。但說到底,還是如何把國家的建設和個人的生活、日常的空間緊密聯系起來。我在大慶調研的時候,始終被很多曾經在那里生活和工作過的大慶人所深深打動。在那個創業的年代、開拓邊疆的年代,我們去看那時候人們的照片,眼中都是閃著光芒的。在接觸了許多大慶人之后,我把目光聚焦于一對上世紀50年代從同濟大學城市規劃專業畢業的大學生,曉華和阿松夫婦身上,他們的故事與書中的每一個章節平行展開。”
曉華和阿松在大慶的第一個家:薩爾圖的“科學干打壘”
“之所以選擇他們,首先是他們手中有第一手的資料,包括當時的信件、日記。另外,曉華作為我在同濟大學的師姐,她是一名女性、一位規劃師,也是一名妻子,一位母親,從1962年到1975年間一直工作生活在大慶,她在理性和情感間,在對專業的追求和家庭的責任間不停地轉換角色,很容易就讓我產生共情。”侯麗說。
“1963年,大慶的領導決定建造‘干打壘’來永久性解決住房問題,曉華所在的大慶油田土木工程第四室接到的任務是設計出‘科學干打壘’,一種可以存在‘至少五十年’的土坯房。今天再看那時的設計圖紙,我們很難體會到當年這些從中國最好的大學建筑專業畢業的設計師如何花費了幾年的時間去完成這樣一種建筑,包括干打壘村的建造。”侯麗說。
第一個“科學干打壘”村:紅衛星村
在她看來“科學干打壘”體現了那時的美學。“這是一種用生土、干草,石油生產瀝青、油渣,這些最簡單的材料和木材的邊角料所形成的突破材料本身最大可能而形成的結構和構造,設計師卻盡可能賦予它曲面的線條。當時一方面要抓石油生產,同時這批人還要在大慶墾荒,突破資源的不足,于是形成了大慶工農村特有的場景。他們改變了居住的模式,改變生產生活關系的模式,又進而影響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和家庭之間的關系,以及人和集體的關系。”
現代地理學家大衛·哈維有句話,“場所營造是一種包含了物質、表征和符號的政治活動。”侯麗介紹說在大慶,前后有三代“鐵人紀念館”。“在大慶除了有居住建筑,也有公共建筑。鐵人是大慶的模范和典型人物,第一代鐵人紀念館是阿松在1975年離開大慶前設計的,2008年我去到大慶的時候,阿松設計的紀念館已經變成了一個建材市場。你會看到這處清水磚墻的建筑樸素地幾乎沒有任何裝飾,但在頂部依然是‘鐵人帽’的造型。和大慶當年所有的公共建筑一樣,這里的廁所只有小便池,沒有大便池,大便一定要在室外的旱廁解決,要‘為革命積肥’,體現出服務農業生產的特征。”
1976年,大慶人在阿松設計的鐵人王進喜紀念館前慶祝“四人幫”的倒臺
“總結一下,這本書是我嘗試去講述在一個國家和社會關系的發展過程中,一個特定的石油工業城市的故事。它涉及到非常多的話題,包括資源、性別、個人和集體,城鄉關系、政治、空間形態,以及特定的干打壘這樣的建設形成,是如何集中展現當時各方面的張力和矛盾的。而當所有的‘堅固’都煙消云散,仍然有一些看似不那么‘堅固’的東西始終存留在當下,跟我們發生著固定的聯系。希望大家從不同的視角去理解大慶,從大慶人身上的勇氣和韌性中會得到更多的啟示。歷史不僅僅是記錄、重構或者再現,歷史也讓我們相信變化是會發生的。”侯麗最后說道。
“工業遺產更重要的價值是作為一種見證”
“我讀這本書就像是重溫了一遍歷史,說大一點是補了這一段歷史的‘課’,侯麗把中國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工業史以案例的方式鮮活地展示出來。我這個年齡段的人,對那時的生活場景還有些感受,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就沒有什么感覺,其實這段歷史很珍貴。”中國城市規劃設計院院長王凱說。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院院長王凱
“第二個感受是這本書的寫法很新穎,體現了大歷史中的人文情懷。這種寫法對于我們如何去理解歷史,理解歷史當中的人是有很大啟發的。全書娓娓道來,反映出的思想還是相當深刻的。對于當下的規劃師而言,書中對當年工業化時代的城鎮化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價值。”
大慶化肥廠,廠房采用了經濟實用的磚砌工業建筑風格
在王凱看來,讀者要注意里面大慶模式的十六字總結,“工農結合、城鄉結合、有利生產、方便生活。”“石油是國家的命脈,大慶的地位之所以重要,其實跟工業化的命門所系有很大的關系。書中提到的干打壘村,在鉆井的邊上建生活區。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一種切合實際的選擇。現在我們來到了新時代,談談經濟發展和城市發展的時候也會提到‘產城融合’,雖然不是要回到當年在工廠邊上建宿舍的模式,但還是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發。講到城鄉一體和城鄉融合,關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道路該怎么去走,我們其實一直在探索之中。”
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嚴鵬回憶說,自己最早關注《大慶:為了石油的建設》英文版時,還以為是歷史專業的學者寫的。“拿到中文版,仔細拜讀之后才發現是規劃設計學者的作品。這本書最大的優點就是把國家的大趨勢和個體命運很巧妙地交織在一起。如此一來,就是用復線而不是單線的形式呈現出歷史價值的多元性。我們都知道工業化是現代化的核心,但工業發展本身不是單純的經濟過程,而是一個綜合性的歷史進程,是政治、經濟的,也涉及到文化的綜合過程。”
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嚴鵬
“大慶在中國現代化、工業化的過程中意義非凡。過去我們提到工業,就會提到‘工業學大慶’,大慶是一個典型和代表。但是‘學大慶’學什么,過去的宣傳更加突出鐵人的干勁和奉獻,一談到大慶就是忘我、無私、奉獻這些語匯。但是它的另一面,它的工業文化、工業精神,以及背后的管理模式,我們可以從今天的大慶石油歷史陳列館包括侯麗的這本書中,看到歷史的敘事已經把技術和科學強調了起來。”
大慶油田在現而今的國家能源安全戰略中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同時作為一處國家工業遺產,如何在文旅熱的當下更好地發揮作用?在場專家也紛紛獻計獻策。一直參與工信部國家工業遺產評選認定工作的嚴鵬認為,物質性的和無形的工業遺產都值得重視。“我們把老廠房、老車間保留下來,它們承載的是什么?當然它們也有建筑上作為文物的有形價值,但更重要的是作為一種見證。除了做工業文旅,我們現在也在做工業文化研學,把青少年、學生帶到這些地方去,去了解歷史、學習精神,了解其間的生存演變。其實在更大的敘事維度,這些工業遺址也承載著企業家精神、工匠精神、勞動精神、工業精神和創新精神。今后很重要的一項工作是把和這些工業遺產相關的普通個體參與者,他們當年的個人史、生活史通過技術手段融合進去。從這個角度上講,侯麗的這本書在工業遺產非物質文化層面的推廣上,做出了一次非常好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