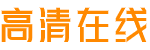2024年7月9日凌晨,知名考古學家、被考古學界稱為“黃頭兒”的黃景略先生去世了,享年94歲。
黃景略和張忠培是1952年北京大學“中國考古第一班”的同學,后者創辦了吉林大學考古專業,擔任過故宮博物院院長和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在今年7月即將出版的張忠培口述史《考古張忠培》中,有一節專門講述了黃景略和張忠培先生的經年往事與如歌歲月。
現蒙口述史整理者、黃景略和張忠培的學生、復旦大學教授高蒙河慨允,先期披露,送別先生。

2010年10月,黃景略在嘉興市申報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工作匯報會上(來源:南湖晚報,攝影:袁陪德 圖片為編者所加)
黃景略是福建惠安人,我們倆是1952年一起考上北京大學歷史系的。那一年,北大歷史系率先在全國高校成立了考古專業,因此我們也就成了中國首屆考古專業的學生。我倆都愛打籃球,他籃球打得比我好,投籃姿勢很標準,當過班上的體育干事。在大學本科田野實習的時候,我們就比較談得來。

北大1952級考古專業同學游覽八達嶺(右一張忠培,右二黃景略)
畢業后,我留校讀了副博士研究生,他去了文化部文物局。黃景略和我一樣,大學畢業時想做研究,不想搞行政,他還給文物局和教育部領導寫信,結果都落到了時任文物處長陳滋德手里,想走沒走成,只好留了下來。后來又擔任文物處處長,做過國家文物局副局長。他還是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組組長,我是專家組成員。
黃景略去文物局之前,中國的考古工作主要靠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各個地方單位,并不上報中央主管單位,而且那時文物局也沒有考古處,只有文物處。這種松散的管理結構,勉強維持著新中國當時非常薄弱的考古工作。
他剛分去時,文物局的裴文中、羅福頤、顧鐵符、羅哲文、莊敏、劉啟益等22人中,有做文物保護的,有搞書畫鑒定的,黃景略是分到文物局工作的第一個考古專業畢業生。
當時各地考古專業人員不多,也不夠,懂考古的管理工作更缺,規章制度也都沒建立起來。他除被派去或抽調協調地方重大發掘項目以外,也做些人才培養工作,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北大等大學畢業的考古專業學生,大多在他手下接受過訓練。比如1958年山東舉辦臨沂、泰安文物干部訓練班,黃景略就去當教員,為學員們講課,還帶隊到山東日照兩城鎮遺址現場實習,負責實際勘探和試掘。文物訓練班的辦學效果讓黃景略意識到,人才培養,是發展考古事業的先決條件。
我創辦吉大考古專業期間在北京的事大多都是通過他來聯系和溝通的。而且,當時吉大歷史系支部書記李木庚也和他熟悉起來,吉大考古的很多事,特別是進入關內的考古實習、考古基地建設都是我們三個人聯手促成的。
黃景略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當年我到北京出差,必住他家,只為做徹夜長談。那時的條件,也就一個單人床。夜深了,我們倆就一顛一倒臉對著腳,同榻而睡,抵足而眠,好在也睡不了幾個小時。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大家的生活條件都是很差、很困難的。我經常出差,家里有三個孩子,又不可能雇保姆,妻子馬淑琴常吐槽我當時只顧打拼,顧不了家,她帶孩子很不易。有時因為孩子沒人照顧,我出差也會帶孩子來北京,放到黃景略家里,交給他夫人蘇文錦老師。我這三個孩子都在黃景略家里住過。可以說,為了考古,為了事業,我們那一代人真是把家庭都放在了第二位。
黃景略懂考古,管考古,是我國考古走向管理科學化、操作規范化、工作制度化的親歷者和見證人,在考古界有很多功績:
第一個是六十年代主持山西侯馬晉國遺址的發掘工作。1960年前后,某大型企業擬在侯馬晉國遺址建廠,國家文物局派黃景略前往支援,負責發掘工作。他在發掘的基礎上對侯馬晉國遺址做過一些綜合性研究,主編了《侯馬鑄銅遺址》,1995年還獲得夏鼐考古學研究成果一等獎。后來考古界對晉文化的大規模研究,是從他那里開始的。

在1960~1964年間,黃景略先后主持了侯馬鑄銅遺址幾個主要地點的發掘,圖為測量22號地點(1963年)。(圖片為編者所加)

1962年冬蘇秉琦先生在侯馬工作站與參加發掘的人員合影。前排左起:張萬鐘、曹定云、齊惠芬、羅坤 后排左起:黃景略、吳振祿、王克林、陶正剛、蘇秉琦(左7)、王巖、溫明容、勞伯敏(右3)、戴尊德、楊富斗(圖片為編者所加)
吉大考古實習黃景略也沒少參與指導,親自帶工地。黃景略的田野考古尤其是對城址的勘探發掘,水平是一流的,我看到現在為止恐怕也沒有什么人真能超過他。對于城址考古,他能自己動手,掌握大面積的剖面及平面,我很佩服。后來我倆一起在太谷白燕遺址發掘,楊建華回憶工地上的黃頭兒在尋找土色變化時常用的動作,就是摘下他的草帽把陽光擋住,仔細地辨析著土色的變化,嘴里還念念有詞地說著:“怎么不靈光了?”
第二個貢獻是燕下都遺址的發掘搞出來了一個格局。黃景略在燕下都主持發掘工作時,親自管理探工,教探工如何勘探。我們現在很多考古工地都是聽探工說話,說什么是什么,也不親自勘驗,那怎么能搞好考古工作呢?
吉大去燕下都發掘,也和他有關。1975年,湖北江陵楚紀南城地區大搞農田建設,危及城址的保護。國家文物局叫吉大考古專業參加,派黃景略協助我們工作一年多。1976年初,紀南城30號臺基發掘實習告一段落,大家都撤了,我本留在工地準備等馬淑琴會合后一起回長沙老家過年。哪成想馬淑琴沒到,卻接到李木庚電報,叫我回長春。原來,陳滋德處長轉告現在河北易縣燕下都遺址也在配合農業學大寨,興修水利深翻土,有可能破壞地面古跡,要搞考古勘探和發掘,希望吉林大學能去。
于是我回長春簡單過了個年,剛到初四,李木庚就邀我赴易縣。就這樣,受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的委托,我們組織75級學生和部分73級學生,和河北省文物管理處共同發掘了易縣燕下都遺址,搞清了此地自商至漢代的堆積和燕下都遺址本身的文化分期。
第三個貢獻是參與制定文物局關于考古方面的規章制度。早在侯馬遺址的考古實踐中,黃景略便具體負責業務工作,他給考古隊擬定了田野發掘的具體要求、工作步驟以及發掘記錄的格式,作為田野考古工作的規程,以便大家統一認識,使發掘清理有了規矩,保證了田野考古的科學質量。之后他將所思所想匯聚成具體條文,把田野考古和室內整理做了十幾條規定,成為后來全國通用的《田野考古工作規程》的雛形。
1982年,黃景略升任文物處處長,負責全國的考古工作和文物保護管理。當時隨著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以配合基本建設為主的考古發掘項目大規模增加,大量重要考古新發現集中涌現。盡管當時已經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也開始正式頒發考古發掘申請書和考古發掘證照,但是全國各地考古隊伍狀況參差不齊,青黃不接,田野發掘質量、資料整理和編寫報告以及人才培養等,都成為制約的短板。
于是,1984年3月國家文物局在成都舉辦第一次全國考古發掘工作匯報會,會議由黃景略主持,夏鼐、蘇秉琦都發表了講話,北大嚴文明、吉大的我等70多人參會。
會上討論了三件事:一是聽取前一年全國各地各種考古項目的成果匯報;一是討論制定《省級文物考古機構工作條例》,一是討論制定《田野考古工作規程》。這三件事都是開創性的,對其后中國考古的學術、事業和人才隊伍發展,影響深遠。
會議一結束,黃景略和我自重慶沿長江順流而下,同行的還有賈峨、葉學明、張學海、楊育彬、趙殿增以及吉大剛畢業在文物處黃景略手下工作的王軍、李季等。那時走三峽到宜昌要三天三夜,船上的四等艙一個大通鋪,就成了我們這些人的會議室。受蘇秉琦講的佛、法、僧比喻的啟發,我倆領著大家從討論李季起草的《田野考古操作規程》開始,深入研究加強中國考古發掘管理的科學水平,如何保證工作的質量及考古隊伍建設等問題,哪些該管,哪些不該管,逐漸清晰,收獲頗豐。此后,1984年《田野考古工作規程》由文化部發布試行,全國統一執行,直到2009年才重新修訂。

《田野考古工作規程》起草團隊成員在四川考察(右四張忠培、右六黃景略、右七李季)
第四個貢獻是辦田野考古工作領隊培訓班,培養考古專業人才。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配合基本建設的任務日益繁重,能夠承擔發掘的一線人員比較缺乏,有的甚至還不是考古專業科班出身的。面對這種情況,黃景略說:“那就辦個考古領隊訓練班,有領隊資格才能做考古發掘!”
我倆一拍即合,共同策劃并舉辦了考古領隊培訓班。1984年,國家文物局第一期培訓班在山東兗州西吳寺遺址開班。為了打造考古界的這支被蘇秉琦形容為“北伐”時葉挺的“鐵軍”,他親自做班主任,我、俞偉超、嚴文明、吳汝祚、鄭笑梅、葉學明、孔哲生、張學海等培訓班老師費盡心機、絞盡腦汁的設計出一整套完整的培訓考核制度、規劃和考古工作細則。加上又有國家文物局的李季以及張文軍、喬梁、山東文物考古研究所何德亮的協助,工作進展很順利。
領隊班以田野考古發掘為基礎,對發掘資料整理、編寫考古報告進行全流程訓練。黃景略親自指導發掘、整理報告和答辯。在設計制度時大家一致同意為了保證質量,考核必須有淘汰制度,不及格者要再回爐重新學習。鐵軍嘛,鐵的紀律,鐵的作風,鐵石心腸,慈不治軍。
培訓結業答辯是大戲。1984年12月我到兗州,李季開車來接我,他知道我肯定要做最鐵的“鷹派”考官,在開車接到我之后,接話趕話,趁機說情。
他鋪墊說:“先生您來了大家都特緊張。”
我感覺得出來他是受了學員之托,就想堵住他的話頭,說:“緊張什么,最多不就是不及格嘛……”
考官中我和黃景略是“鷹派”,俞偉超和鄭笑梅是“鴿派”,兩派對壘,劍拔弩張,爭執下來,還是聽老黃和我的。領隊班最為核心的考核要有淘汰機制,不及格者重新回爐再訓,第一期培訓班有四分之一的學員未通過考核。
李季在他的日記里,記錄過考核的過程:
兗州西吳寺工地第一期考古領隊培訓班結業典禮的聚餐早已曲終人散。載著哭別學員大客車前天開走了。載著已經平息了激動與爭執的教授們的面包車昨天開走了。
學員和教授們走時并不是興高采烈的,我提筆填寫無記名投票結果時,是極端沉重的。這一切陰影,來源于我們這個班有淘汰率,而且高達四分之一!
于是,人們會憐憫、痛苦、內疚,甚至是憤怒,這是否太殘酷了!真的是很殘酷的,在考核教師“鷹派”與“鴿派”激烈辯論并訴諸表決之后,結論仍然是這樣殘酷,以致俞偉超和鄭笑梅老師大動感情,泣不成聲,以致我也不忍把這消息告訴落選者本人。雖然我知道,更殘酷的是,多年沒有淘汰的制度,腐化和窒息了我們的社會和我們的事業。
我對張忠培老師說,我這三個月的鍛煉,遠遠大于三年……
領隊班前后辦了近十期,培訓了數百人,分布在全國大部分省、市、自治區,擔負起第一線的考古發掘工作,促進提高了田野發掘質量,得到了業界的普遍贊譽,后來黃景略還主持建立了考古發掘領隊的審批制度,延續至今。

1981年,1952級三個同班同學共同主持山西太谷白燕工地(右 張忠培,中 黃景略,左 王克林)
第五個貢獻是對于全國文物的保護,以及對于一些與文物保護有關的考古發掘工作,他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黃景略他個人寫的論文不多,但他對遺址保護、文物局規章制度方面,以及文物局發生了哪些事情,可以說是一部活字典,來龍去脈都能說得清清楚楚。
第六個貢獻是,組織和主持編纂出版了《中國文物地圖集》。
吉大辦學起步到后來進入關內發展那些年來,我從黃景略那里得到的幫助也特別大。黃景略對吉大在張家口和晉中的兩個考古基地,有個評價:
“(吉大)實習基地的建設,有如下幾方面的收獲:
(1)大大改變了那種打游擊戰的實習方式,使學校的教學計劃得到保證實現;(2)把教學實習和科學研究緊密結合一起,減少盲目性和被動性;(3)學生的實習訓練全面深入規范化:(4)指導老師的考古實踐水平和科研能力得到提高,高于其它學校的同代人;(5)獲得一批科研成果;(6)培養了一批技術水平較高的技術工人,他們在支援其它地方的工作中,傳播了技術。建立考古實習基地的做法,已得到國家教委的贊賞和國家文物局的支持,一些學校也開始效仿。”
他的這番評價,雖然說的是吉大,可我卻看見了他在我們共同創業過程中的那些日日夜夜,那些并肩戰斗,那些苦辣酸甜。正是在黃景略全力參與、籌劃、支持下,依靠這種友誼、團結和艱苦奮戰,才看到一批批合格的學生走出了工地,一批批年青教師成長起來,一批批的系列性科研成果發表出版,吉林大學考古專業才邁上了一個新臺階,逐漸形成了學科建設的吉大模式。
吉大考古專業之所以能走到今天,發展成為國內頂尖、國際一流的特色專業。除了參與辦學的同事忠誠于教育事業,實現了團結、奮斗的精神外,重要的是得到了學校特別是李木庚及同仁們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和湖北、河北、山西、甘肅、青海、遼寧、內蒙古、北京及吉林、黑龍江諸省市的文物、考古機構及其同行們的通力合作和鼎力支持。

1995年,張忠培和黃景略在黑龍江考古工地
我作為最主要的創業者、親歷者和當事人,現在回想起來這一過程可以說是曲折跌宕,頗具傳奇色彩。那些老一輩、中年一代、青年考古學者的形象,從我回憶的腦海中蹦出,還匆匆不停地在眼前閃現,想起他們,想著以往的路,使我難以抑制對那些曾給予我熱情關懷、指導和友誼援助的諸師友的感激之情。
從互為同學,到互相支持,從互為同道,到互相成就,這就是我和老黃的人生和情義。
那老黃為什么被考古界俗稱為“黃頭兒”?可能與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引進的一部美國電視劇《加里森敢死隊》有關。那部劇里的敢死隊員們,動不動就把隊長加里森中尉叫做“頭兒”。
老黃在文物局當處長的時候,吉大畢業的王軍、李季他們幾個年輕人剛分到局里,做了老黃的部下,“黃頭兒”就被喜歡新奇、時髦、江湖、個性的年輕人們叫開了。叫到什么程度呢?叫到年輕人可以當面叫他“黃頭兒”,他不生氣;叫到知道“黃頭兒”的人,比知道黃景略大名的人多得多。
但我從來都不叫他“黃頭兒”,我就叫他老黃,他就叫我老張,我們倆就這樣互相叫了一輩子。